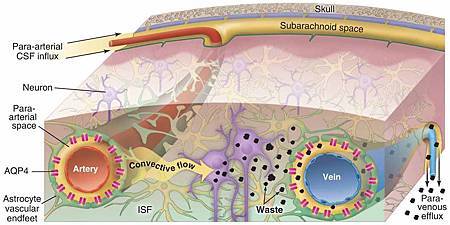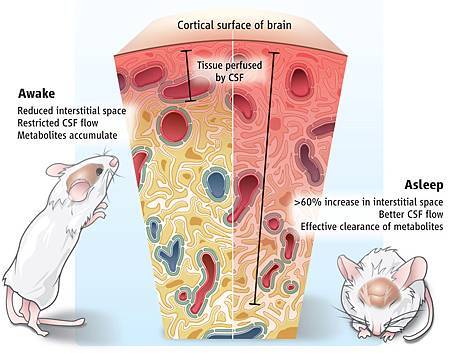你有想過你會因為施打了生長激素而感染到阿茲海默症嗎?阿茲海默症是會傳染的嗎?
何謂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是失智症的其中一種,主要病徵是大腦中有 β-amyloid (Aβ) 和 tau 蛋白堆積。
該病又分為早發性(early-onset)和晚發性(late-onset, LOAD)。
早發性是遺傳造成的,主要是因為 PSEN1 (presenilin 1)、PSEN2 和 APP (amyloid protein precursor) 帶有突變,導致 β-amyloid (Aβ) 的其中一種 — Aβ42 結塊(aggregates)和堆積,加上 tau 的堆積而引起的,通常在四、五十歲左右就會出現症狀。除此之外,APOE4 也被認為是阿茲海默症相關基因,帶有兩個 APOE4 基因的人患病風險較高。
晚發性的病因則不清楚,目前認為老化是主因,隨著年齡增長 Aβ 錯誤折疊機率越高,進而導致 Aβ 堆積,通常都是六十歲之後才開始出現症狀,65 歲以後患病風險每五年大約增加一倍。
除了老化以外,其他可能原因包括感染和發炎導致 Aβ 堆積,其中被認為可能導致阿茲海默症的感染是皰疹病毒。
相關文章:
阿茲海默症真的和皰疹病毒有關嗎?
不過,2016 年的一篇研究掀起了一個熱烈的討論:阿茲海默症是否跟狂牛症和庫賈氏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的普利昂蛋白(prion)一樣會傳染。
Aβ 堆積是怎麼開始的?
已知基因變異導致的 Aβ42 摺疊錯誤會造成堆積,但堆積是怎麼開始的並不清楚。
有個理論是 Aβ 堆積需要一個折疊錯誤的 Aβ 做為種子,有了種子就可以引發一連串的結塊,進而造成堆積。
2006 年的時候,
有篇刊在 Science 的研究是把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腦部萃取物注射到阿茲海默症老鼠腦中,可以使老鼠老鼠腦中出現堆積。如果把腦部萃取物中的 Aβ 移除或減少,則會減輕堆積的程度。
之後
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研究顯示把 Aβ 加入培養的神經細胞中後,也會造成 Aβ 結塊堆積。
加州 UCSF 的研究則是把大腦萃取出來的 Aβ,或是合成的 Aβ 注射到阿茲海默症老鼠體內,結果發現兩者皆可在老鼠腦中形成 Aβ 結塊堆積。
這些結果皆暗示 Aβ 的自我擴散(self-propagate)能力跟造成狂牛病的 prion 很類似。
傳染爭議的起源:生長激素
阿茲海默症會傳染的想法是從哪裡開始的呢?
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 GH)被用來治療生長激素嚴重不足(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GHD)的孩童。
英國在 1958 年到 1985 年間,從過世者的腦下垂體(pituitary gland)中萃取出生長激素(cadaveric-derived human growth hormone, c-hGH)用於治療,在那 27 年間英國至少有 1,848 名孩童施打過生長激素,全球則有約三萬五千位孩童接受生長激素治療,直到 1985 年的時候,美國 FDA 收到報告說有四位曾經接受 c-hGH 治療的成人得到 CJD [註] 後才停止。
註:prion protein (PrP) 是哺乳類動物本生就有的蛋白(cellular PrP),當其基因 PRNP 發生突變導致錯誤折疊(misfolded)的時候,scrapie PrP,便會引起腦神經性疾病且具傳染性,在牛身上會引發狂牛症(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在人類身上則會造成 CJD,是一個顯性遺傳的疾病。從外界或醫療介入(例如手術)得到的情況很罕見,大概只佔了 1%。
研究發現這些生長激素在準備過程中被 prion 污染了,導致到 2012 為止,在所有共 450 位的 CJD 病患中,有 226 位因施打生長激素感染到 CJD,其中有 80 名孩童在英國。
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神經學家,同時也是研究主持人 Dr. John Collinge 和他的同事檢視了其中八位年齡在 36-51 歲之間,因為 CJD 而過世的病患腦細胞組織。這些患者在接受最後一劑生長激素治療的約 19 年到 31 年後,才因 CJD 發病過世。
但讓人訝異的是檢驗後發現其中有四位的腦中除了有 prion 外,其腦部還有嚴重的 Aβ 堆積,有兩位是局部的 Aβ 堆積,只有一位完全沒有 Aβ,而這些人都還只是中壯年而已(36-51 歲),並且未帶有阿茲海默症的致病突變,腦中有澱粉樣蛋白 Aβ 堆積是非常罕見的情況。
Collinge 也檢視了其他 116 位沒施打過生長激素的 CJD 病患,看有沒有人同樣有 Aβ 堆積,但沒人有同樣的徵狀。
那這些施打過生長激素的患者為什麼會有阿茲海默症的病徵?
的確有幾批生長激素有 Aβ 污染
之前的動物實驗顯示,把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腦漿注入老鼠腦中,會使老鼠得到阿茲海默症,因此透過被 Aβ 污染的生長激素也可能感染到接受生長治療的孩童。
為了證明這些患者會得到阿茲海默症,是因為施打了被 Aβ 污染的生長激素,他們找到了當年帶有 prion 的那批生長激素 -- 雖然已過了三十多年。
當時準備生長激素的方法有很多種,純化過程有過 size exclusion column (SEC) 的被認為可以降低 prion 的污染,而其中有一種萃取法為 Hartree-modified Wilhelmi procedure (HWP),是沒經過 SEC 這個步驟的,當初接受治療且得到得到 CJD 的病患用的那批 c-hGH 都是用 HWP 方法萃取出來的。
他們從英國的 Public Health England 那得到了當年的那幾批生長激素,然後檢測裡面是否有 Aβ 和 tau,結果發現所有用 HWP 方法萃取的 c-hGH 都含有較不易結塊的 Aβ40 和 tau,而用其他方法純化的則沒有檢測到任何 Aβ 和 tau。另外,他們取得的五罐用 HWP 純化的生長激素中,只有一罐沒有會結塊 Aβ42 以外,其他的也都有 Aβ42。
### 被污染的生長激素會傳染阿茲海默症嗎?
再來就是檢測這些含有 Aβ 和 tau 的生長激素是否真的能在體內引發 Aβ plaque,他們用的是帶有人類 APP 突變的基轉老鼠,這些老鼠會在六個月大的時候開始出現 Aβ 堆積的徵兆。
阿茲海默患者的腦部萃取物會引發 Aβ 堆積
他們先用患者的腦部萃取物試驗,把取得三位 AD 患者的腦部檢體和一位健康者的腦部檢體,分別打入六到八週大的基轉老鼠腦內,腦部檢體是用 PBS 準備的,所以有一個控制組是只打入 PBS,每組有十五隻老鼠,之後在打入後的第 2, 7, 15, 30, 45, 60, 90, 120, 240, 360 和 480 天的時候檢視老鼠腦部看有沒有阿茲海默症的其中一個病徵:cerebral Aβ−amyloid angiopathy (CAA) -- 腦部血管出現 Aβ 堆積。
結果顯示施打後的第二天所有老鼠都沒有 Aβ 堆積,表示起始點是一樣的。
但是,在打入腦部檢體 120 天後,被打入 AD 病患腦部檢體的老鼠,牠們的腦部的某些區塊 -- 像是大腦皮質和海馬迴 -- 開始出現 CAA,而只打入健康者腦部的和 PBS 的老鼠都沒有出現 Aβ。接著在 240 天(約七、八個月)後,老鼠的腦血管裡出現 Aβ,堆積情形以小腦最為明顯。同樣的,打入健康者腦部檢體的和打入 PBS 的老鼠幾乎沒有 Aβ 堆積的情形。在打入 AD 腦部檢體快一年後的情況和 240 天後的差不多,只是堆積情況更嚴重些。
這個結果看起來是滿有力的證據,不過我覺得他們如果有用其他非 HWP 純化的 c-hGH 當做控制組會更有力。另外要注意的是外來的(exogenous) Aβ 並沒有在正常老鼠腦內引起堆積,而是在帶有 APP 突變的基轉老鼠裡,表示要個體本身就有得到 AD 的風險,外來的 Aβ 只是加速疾病的發生和進展。(也許加入表現人類正常 APP 的基轉老鼠當控制組會比較好)
三十年前的生長激素也會引起 Aβ 堆積
再來,他們想確認人類的生長激素本身會不會對老鼠有影響,所以先用 recombinant hGH (rec-hGH) 做測試。
他們打入不同濃度的 rec-hGH 到基轉老鼠腦中,然後在打入後的 240 天後檢測,都未發現有什麼影響,只有在打入高濃度的 rec-hGH 後老鼠立刻死亡。
接著便是測試放了三十幾年的 c-hGH 是否能在 AD 基轉老鼠腦中引起 Aβ 堆積。
因為剩下的 HWP c-hGH 量並不多,為了有效利用,他們選擇直接打入老鼠的腦部(當初的孩童是由皮下打入),同時也用 rec-hGH 當作控制組,確認生長激素本身並不會引起 Aβ 的堆積,不過打入的 rec-hGH 劑量比 c-hGH 較多。在這個實驗中,他們有加入另一組控制組,就是把人類腦部檢體、PBS 和 c-hGH 也打入六到八週大的野生鼠(只有老鼠本身的 APP,沒有人類的)。
他們在施打後的 240 天後解剖檢視,發現所有野生鼠都沒有 Aβ 堆積的情形,被打入 rec-hGH 的 AD 基轉老鼠腦部也沒有出現 Aβ 堆積和 CAA 的情形。但是呢,被打入 HWP c-hGH 的老鼠腦部有明顯的 Aβ 堆積和 CAA,表示 Aβ 本身是個種子,可以在其他動物體內引起 Aβ 堆積,而且即使過了幾十年都還保有這個特性。
這個結果看起來是滿有力的證據,不過我覺得他們如果有用其他非 HWP 純化的 c-hGH 當做控制組會更有力。另外要注意的是外來的(exogenous) Aβ 並沒有在正常老鼠腦內引起堆積,而是在帶有 APP 突變的基轉老鼠裡,表示要個體本身就有得到 AD 的風險,外來的 Aβ 只是加速疾病的發生和進展。(也許加入表現人類正常 APP 的基轉老鼠當控制組會比較好)
打過被污染的生長激素後,還存活著的患者有得到阿茲海默症嗎?
那些接受被 Aβ 污染的生長激素的患者,目前還存活的人,現在怎麼了?
他們找到了八位小時候有接受過生長激素的患者,他們當年被施打的生長激素都是用 HWP 方法純化的。
這些患者大多不帶有致病基因,只有一位患者帶有一個 APOE4,而三位沒有基因資料的則沒有早發性阿茲海默症家族史。在檢視了小時候的智力、生長激素治療後遺症、生長激素不足症本身和基因後,都沒發現會導致阿茲海默症的相關性,但是他們在成年後皆出現早發性阿茲海默症症狀。

另外,接受到的生長激素是沒污染的那些幼童,並沒有通報,這也暗示著接受生長激素本身是沒問題的。
也就是說,這些人會患有阿茲海默症極可能是因為施打了被污染的那幾批生長激素而獲得的。
他們發現,經由生長激素得到的阿茲海默症,發作得比遺傳性要早,且認知力衰退的進程也比較緩慢,通常都超過十年。經由生長激素得到的阿茲海默症症狀和遺傳性及偶發性的不同,可能是因為 Aβ 的種類不同。
總結
雖說阿茲海默症是有可能透過醫源性傳播(iatrogenic transmission),但目前已經不用這種方式取得生長激素,外科手術本來就會注意器具清潔避免感染,大家無須太過恐慌。今年有篇 UBC 的研究顯示健康老鼠在接受了阿茲海默症老鼠的骨髓移植後,腦中出現了 Aβ 堆積和記憶力衰退的現象,雖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確認,不過如果把這個可能性考慮進去,未來在各方面多一層防範不是壞事。
Articles:
Alzheimer’s disease may have been transmitted in now-banned hormone treatments | Science | AAAS
Bone marrow transplants spread Alzheimer’s-like disease in mice, controversial study reports | Science | AAAS
References:
VS Ayyar, History of growth hormone therapy. Indian J Endocrinol Meta (2011)
SA Purro et al, Transmission of amyloid-β protein pathology from cadaveric pituitary growth hormone. Nature (2018)
Z Jaunmuktane et al, Evidence for human transmission of amyloid-β pathology and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Nature (2015)
G Banerjee, SF Farmer, H Hyare et al. Iatrogenic Alzheimer’s disease in recipients of cadaveric pituitary-derived growth hormone. Nat Med (2024) DOI:
10.1038/s41591-023-02729-2
☕️
如果你喜歡這篇內容,歡迎賞一杯咖啡。😊